腎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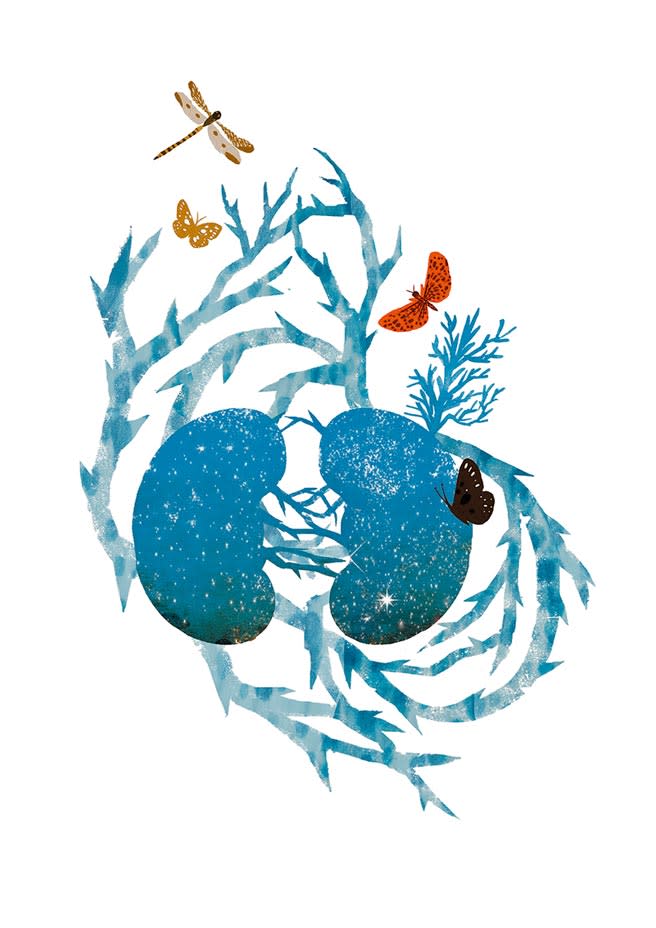
八有老解的「前車之鑒」,孫義璽非常清楚,能救他的辦法只有兩個:終生透析或者換腎。
老解在家裡呆了四天,身體開始出現意識障礙、嗜睡、昏迷,學名叫:電解質紊亂。他不得不進入離家最近的縣醫院,一針利尿劑讓他排空體內多餘的水之後,隨之而來的檢查結果告訴他,必須要住院治療,並且,最好到省城。
同時,他也清楚了利尿劑的作用正是在他腎臟無法工作時的強制之舉,最讓他絕望的,是醫生將中醫療法一棍子打死:「與肝肺細胞不同,腎小球是無法再生的。」
他必須接受自己的腎臟完蛋的事實。
老解在父親的陪伴下回到了家,逕直回屋躺在了床上,母親和妹妹就圍了過來,迷迷糊糊中,他感到一絲死亡的氣息,幻象中,身邊的親人,都成了收屍者。
他害怕了,強忍著病痛和清晨一同起來,在省城的醫院裡,簡單檢查,一夜時間,肌酐從1180升至2448。他第一時間被送進了透析室。
這家蜚聲全國的醫院,從建院開始,最高的記錄曾是1686。
九
孫義璽怕得要死,恐懼和死亡的陰影圍繞著他。一星期後,我提著一袋子蘋果來到他的病房,裡面還有我們共同的朋友舒志傑、王建。
他看上去沒有想象中頹靡,或許和早上剛透析完有關,替代腎臟工作的透析機清除了他血液中的毒素,讓他暫時輕鬆,雖然幾天之後,沉積在血液中的毒素需要再次清理,周而復始。幾句簡單寒暄後,大家陷入靜默。他的未婚妻洗了三個蘋果遞給我們,推讓中,他才又恢復了點活力。
病房內有三張床,孫義璽占中間,左邊床上躺著一位約莫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閉著眼睛,不知道有沒有睡著。右邊的床是空的,有人躺過的痕跡,不一會兒,一名中年婦女走了進來,將手裡的塑料袋放在那張床旁邊的白色櫃子上,我起身,將屁股下的凳子拿給她。
「你坐著,沒事。」
話音未落,一個和孫義璽年齡相仿的病人走到那張空床邊,幾秒鐘後,他躺了下來。
「陽台坐會兒吧。」 孫義璽起身,帶我們來到病房後門連通的陽台上。所謂的陽台就是病房後門的過道,十幾間病房連城一片,醫院把它像陽台一樣封了起來。旁邊病房的家屬三三兩兩在陽台上抽煙。
「想辦法弄點捐款。」孫義璽突然開口。
十
捐助是重症司空見慣的有效辦法,早在老解住進醫院之後,他藝術圈的朋友們就在外整天忙乎為他捐款的事情。一幫行為藝術家走上街頭,做著在常人看來無法理解的行為藝術作品。有點資源的朋友,紛紛在網絡上發布老解的求助信息。各路匯集的錢統計在一起,與昂貴的醫藥費比起來,仍杯水車薪。
老解是幸運的。一位不願意透露身分的藝術家將一筆足夠老解進行換腎手術及術後一段時間醫藥費的捐款打入他銀行卡上的時候,老解不得不服用降壓藥來緩解震驚帶給他的不安。
更為幸運的是,三個月後,一聲槍決過後,等候在刑場的醫生將死刑犯的腎進行灌注處理後,將腎放入裝滿冰塊的盒子裡,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手術室。與此同時,已麻醉的老解已經躺在了手術台上。
手術之後,走出隔離室的老解看到新鮮的尿液終於不再是礦泉水般的純淨色,捧在手裡靠近鼻子,一股腥臊的氣味告訴他:他活了。
如今體內裝著三個腎的老解已經走過了換腎之後的第四個年頭,除了一些需要忌口的東西,已和常人無異。孫義璽就是在老解換腎之後的第四個年頭患上了和老解一樣的病,加上老解幸運到可以成為傳奇的經歷。孫義璽同樣希望自己能夠順利得到一顆健康的腎源,也能從天而降一位好心人,解決他病中一切的費用問題。捐款成了必須。
十一
從天而降給孫義璽捐助巨款的人還沒出現,他未婚妻就跑了。
那天一大早,孫義璽去做完透析已經中午了,未婚妻陪他回到病房之後說回家拿生活用品,孫義璽等了一下午,覺得情況不妙,他向護士請了幾個小時假,回到家,未婚妻和一切屬於未婚妻的東西,都不見了。
他知道發生了什麼,電話關機,當然信息也不會回,孫義璽看著那些空置的地方,灰塵和時間證明它們確實存在過,比生病更大的一種絕望從地面爬上他。
他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他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車回到醫院,給所有認識他未婚妻的人訴說發生的事情,並希望他們在自己能夠聯繫到的範圍內得到未婚妻的一絲聲音。
這些人中,包括我。
結果是一樣的,無聲的靜默存在了兩天,然後,所有認識他未婚妻的人再也聯繫不到她。她刪除了他身邊朋友和家人的所有聯繫方式。
這樣的結果,孫義璽想到過,悲觀的人對悲傷的事情總有莫名的直覺。未婚妻的父母曾坐了九百多公里的火車趕到醫院,看望他們未來的女婿,從他們冷靜的舉止中,他意識到這件事最終的結局。
事實發生後,孫義璽言之鑿鑿:
「他爹媽根本不是來看我的,就是來看他們女兒的,看她是否承受得了。」
「順便看看我是不是快死了,好讓女兒趕緊放手。」
「我一點都不怪她,誰會嫁給一個尿毒症病人。」
髒話、嘆息、陰陽怪氣中的憤怒、絕望、嘲笑在他內心播散開,在阻止這些情緒播散的地方,通通被割裂出傷口。
「我真想找個妓女,給她幾萬塊錢,給我生個孩子,完事她走人。」曾經說出這話的老解在孫義璽生病的時候,已經走過了婚姻的第二個年頭。他的妻子來自四川,身邊的朋友很少知道他們是怎麼相識的,總之,她不嫌棄他失去的一切。
世上應該沒有完美的幸運,他們結婚之後不久,老解就自己住進了醫院,我以為是他身體出現了排異,急匆匆趕到病房:「住這麼高級的病房。」他沒理我,偷偷帶我出來抽煙。「嚴重嗎?」我邊走邊問。「沒事兒,就想出來呆兩天。」
「出什麼事兒了?」我抽出一根煙,他從我手裡搶了過去放在自己嘴上,我看了他一眼。「沒事兒。」他解釋:「前兩天確實不舒服,住了兩天,媳婦兒天天叨叨耽誤工作、賺錢亂七八糟的,索性多住兩天,清淨。」
孫義璽和他未婚妻再沒有交集,一年後,老解的妻子為他生了一個女兒。孫義璽也沒有碰到過從天而降捐助他的人。
十二
來自農村的孫義璽和老解沒有醫保,對於尿毒症病人來說,醫保確實是減小負擔的重要方式。
老解常給我講他住院期間碰到的各樣病友,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幾乎每天都能見到病房的床位突然空了的情況,這說明病人出院回家了,絕大多數,「回家」不等於出院,醫療費太貴了,回家就意味著放棄,放棄後只有一個結果:死亡。
出院後的老解為了負擔昂貴的藥費,不得不快速調整身體,靠自己的美術專業底子進了一家朋友介紹的高考美術培訓班做老師,他帶的是薪資最高的「包過班」,進入這個班的學生,高考過線的幾率很高。
其中一個學生的母親在政府工作,出於讓老解照顧自己家孩子的目的請他吃飯,飯局上,老解講述了自己的病情,學生母親當即表示,可以把老解的戶口遷到省城。
依靠省城戶口,老解後來回到之前的老闆身邊,將自己的醫保落在了這家只有不到三十個人的小公司。
那是2010年左右,所有重症的病房周圍,都徘徊著販賣醫保的「業務員」,他們告訴所有病人:兩萬塊買一個醫保,一個月生效,終生享用;三萬塊買一個醫保,三天內生效,終生享用。
靠著農村合作醫療緩解經濟壓力的孫義璽動了心,整體算下來,醫保相比農村合作醫療能夠讓他後半生少付出至少一半的錢,這只是粗算,細算下來,還會更多。
但兩三萬的價錢,還是讓他覺得太貴了。
十三
孫義璽剛剛生病的時候,老解隔三差五的會去醫院看看他,順便和熟悉的護士醫生聊天,他倆住過同一家醫院,擁有同一個主治醫師。
僅僅是認識,在醫院所受的待遇就完全不同,護士對他的口氣緩和下來,醫生常常單獨來詢問他的病情,問完就走,好像病房中其他病人不存在。
權衡再三,孫義璽決定把買醫保的錢給醫生,目的只有一個:為了盡早取得腎源。孫義璽算過一筆帳,如果不換腎,他每周要透析兩次,一直到死,其中的花費不可計算,但要能夠換腎,一次性的手術費雖然貴點,以後除了吃藥,就不用透析,長遠來看換腎更經濟。
三個月之後孫義璽有些著急了,在他眼裡,老解就是入院三個月進行的換腎手術,而他,還沒有腎源。
他的主治醫師告訴他如今的腎源已經不像四年前老解入院的時候容易得到,除了死刑犯大大減少,自動捐獻的人寥寥無幾。
孫義璽能做的,只有等。
這一等,遙遙無期。
一年之後,孫義璽放棄了最早換腎的想法,我勸他耐心點,一年都等了還怕什麼。他嫌我不懂:
「我現在一點都不著急,是你不懂這裡面的事情。」
「你懂。」
「聽沒聽過久病成醫?」他點了一根煙,雖然醫生極力阻擋所有尿毒症病人抽煙,但他只打算聽一半:少抽。
「啥意思?」
「就是透析,透析最健康。」
「你是不是透析上癮了?」
「給你說了你不懂,腎換了能不能保證永遠不壞?」
「老解說了,這事兒就是一年看兩年,兩年看五年,五年看十年,十年看二十年,就是說一年只要不出事,可保證兩年不會出事,兩年不出事……
「行了行了。」 孫義璽打斷了我:「你見過二十年不壞的嗎?」
「見過一個十年的,陪老解拿藥的時候,他一個病友,女的。」
「才一個?我還不到三十,就算二十年,我五十的時候壞了咋辦?」
「你是不是害怕啊?」
「廢話,你不怕啊?我大不了透一輩子析,起碼安全不出問題。」
「那得多少錢啊?」
他把煙扔到地上,腳捻了幾下。「我現在不怎麼在乎錢了,一旦有了病,錢怎麼省都沒用,還不如對自己好點,我以前一周透兩次,現在一周透三次。」(待續)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